纷飞的雪
|
吴昕孺小说《鸭语》荣膺2013年度“《海外文摘》文学奖”2014-04-16 09:50:16吴昕孺小说《鸭语》荣膺2013年度“《海外文摘》文学奖”
【获奖作品目录】 【长篇小说】 远东来信/张新科 原载《海外文摘》文学版2013年第11、12期
【短篇小说】 鸭语/吴昕孺 原载《海外文摘》文学版2013年第4期
【散文】 月亮颂/鲍尔吉·原野 原载《海外文摘》文学版2013年第3期 在三教堂酿一缸酒/赵德发 原载《海外文摘》文学版2013年第7期 为一个怨恨者的死亡而悲伤/廖华歌 原载《海外文摘》文学版2013年第2期 杜甫和草堂/赵丽宏 原载《海外文摘》文学版2013年第4期 有一张纸/苏沧桑 原载《海外文摘》文学版2013年第7期 气象睢宁/陈恒礼 原载《海外文摘》文学版2013年第7期
【诗歌】 陕南童谣/刘聪博 原载《海外文摘》文学版2013年第6期
【作者简介】
流年专栏:『昕孺阁』 江山文集: http://www.vsread.com/space/myspace-33587.html 吴昕孺:本名吴新宇,1967年12月出生于长沙县。1985年考入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并开始文学创作,曾为“新乡土诗派”骨干成员。在诗歌、散文、小说、文学评论诸领域均有建树。现为湖南教育报刊社编审、湖南省诗歌委员会委员、中国报业网百人专家团专家、中国传媒创新论坛评委、湖南润帝品牌文化顾问,并担任《中国传媒观察》《诗屋》《格桑花开》特邀主编。2004年参加第23届台北世界诗人大会。2008年获得安徽文学奖、中国“新散文”奖。 【获奖作品:鸭语】 http://www.vsread.com/article-331653.html 一 我正坐在方凳上写作业的时候,天忽然俯下身子,好像在检查我的作业。我全身一紧,在巨大的阴影笼罩下,小小的心脏像车轮一样滚动起来。但无论如何,它滚不出天俯下身来的影子,不仅是我,包括我的爸妈、我家像一只鸟受伤的翅膀的屋檐、宽阔的地坪以及远方的田野、河流、桥梁、群山,乃至万物。我惊讶地抬起头,没有任何恐惧,也许是不懂得恐惧,如果晚上一个人不敢上茅厕那不叫恐惧。我像个小大人,惊讶中透露出某种早熟,仿佛在思考世界的样子;而我嘴里咬着的铅笔正在做着小学四年级的作业。 我和妈妈在同一所小学,我是四年级的学习委员,她是学校的代理校长。据说,校长是个老右派,刚摘掉帽子让他来当校长,前不久又送他到五七干校学习去了。我小时候,一直以为右派是比校长更大的干部,要不,怎么校长会成为右派呢。我听妈妈悄悄跟父亲说起过“老右派”的事,上面划定了学校的右派名额,学校实在选不出,校长只好写上自己的名字。如果不是很有本事的人,怎么会毛遂自荐去当右派呢? 从他们后来的谈话中得知,当右派似乎是一件挺可怕的事。哦,正因为可怕,所以才要摘帽。看来,右派是一顶威力极大的帽子,一戴着它就好些年不得翻身。“老右派”就是这样。妈妈本有机会扶正,父亲坚决反对,他说,你一扶正,离当右派就不远了。妈说,右派都摘帽了,还有什么右派?父亲以一种熟悉而又异样的目光盯着妈妈。我熟悉,父亲总是那样看我。妈异样,父亲从没那样看过妈妈。但父亲很快收回了自己的目光,而不是像盯着我那样,直到我头皮发麻。他只说了一句,“代理”是一个很好的掩护。 我喜欢“掩护”这个词,电影里面经常出现。通常,指挥员都会手持驳壳枪或者冲锋枪,对旁边开机关枪的士兵高声喊道:“你掩护,同志们跟我冲啊!”于是我发觉,负责“掩护”的士兵机关枪必须开个不停,他既不要像指挥员那样到敌人炮火中去送死,又把机关枪开得过瘾得死,真让人无比羡慕。我跟班长匹超曾经有过一次著名的争论,他说在战争片中当指挥员最过瘾,我偏说,做掩护的士兵最过瘾。回到家里,我跟妈提及这一争论,妈笑着说,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当班长,而你只是学习委员的缘故。不知怎地,我觉得妈妈这句话里含有很多奚落的成分,从那时起,我开始对她所有的笑抱着怀疑的态度。 天把身子俯得更低。透过窗户,我看见一大堆乌云从天边像无数只鸭子,朝着我奔涌过来。它们翻过山岭,趟过河流,冲过桥梁,穿过田野,直向我奔涌过来,最近一只鸭子的长喙都要触着我的鼻子尖了。我连忙扔下作业本,踢开屁股下面那张呲牙咧嘴的方凳,向爸妈跑去。 爸妈已从屋里到了外面阶基上。他们面对面站着,相距不到十公分,脸却扭过去望着同一个方向。奇怪的是,他们脸上挂着轻松快乐的笑意。如果只是妈妈这样,我会毫不犹豫地表现出怀疑和不屑。自从妈妈代理校长之后,她的笑里便多了些表演的成分。我仿佛看见那些表演成分在“代理”的掩护下,高喊着“同志们跟我冲啊”,妈妈的笑脸常常成为这种表演的战场,只是我不知道到底能得到什么样的战利品。然而,从来不苟言笑的父亲也笑得那么欣然和轻快,这一战况便决计不像表演那么简单。 妈说:“估计过了峡山口。” 父亲点点头,意见却略有不同:“应该快到罗岭桥了。” 峡山口离我家四里地,罗岭桥离我家不到三里地。我问他们,是什么啊? 他们同时瞧我一眼,没有回答,眼睛仍然看着罗岭桥的方向。我再问,到底是什么啊? 妈说:“你听,听得出是什么声音吗?” 我撮起耳朵。猛然,像一阵飓风刮过来,我的耳朵里顿时充满“踢踏踢踏”的声音。我耳朵周围的肌肉略一松弛,那声音便像有人指挥一样,渐渐小了下去;我耳朵周围的肌肉稍一收紧,那声音又渐渐抬高,不是一声一声地抬高,而是整个一片,像天气好的时候,妈妈晒棉絮,“啪”一下将棉絮甩过晾绳。我耳朵周围的肌肉愈收愈紧,那声音愈来愈高,仿佛一群马在我的耳朵里面奔跑,践踏得我的耳膜隐隐作疼。我不自觉地用双手捂住耳朵。我知道我们这里没有马,我只在电影里看见过马,我问妈,是不是发大水了? 妈夸张地笑了。她这一笑的意外效果是让天伸直了身子,它大约检查过我的作业,没有发现错别字,它直起身子,万物便明亮了很多,好像夜里点燃了灯盏。但现在是白天,没有任何点燃的灯盏,是天点燃了万物,让万物亮堂起来,照耀着自身。 真的发大水了!大水从罗岭桥下的河里窜入田野,褐色的水脊宛如乌云翻滚,顷刻到了我们脚下。 妈回答:“秋天哪里来的大水?到底没有知识。” 父亲终于发言了:“还别说,他这架势,是有点洪流滚滚的味道。” 二 “叫肖叔叔。” 父亲指着他对我说。我没有叫,我望着他的脚下,那就是我刚才听到的“大水”,其实真是一群鸭子,估莫有数百只,排着整齐的方阵。鸭子之间不留任何间隙,并排的翅膀挨着翅膀,前后的头尾相接,移动的时候步调一致,这样它们快速翻山越岭的时候,极像随风飘舞的一匹褐色丝绸,或者春潮涌动的滔滔汛水。 其中有两只奇异的鸭子,脖子特别长,颜色更深,而且越往上越大。我很好奇它的脑袋是什么样子,往上看,却没有发现它的脑袋,取而代之的是两只卷起的黄色裤脚。 原来那是一个人的两条腿,而不是鸭脖子。作为人腿,它们真是瘦如枯柴,跟鸭脖子有得一比,却没有鸭脖子的匀称、清丽。腿上的毛又深又黑,好比灶上挂着的薰肉。军裤很旧,穿在这两条腿上显得太大,即便卷起,也掩饰不住里面的空荡。如果不看两条腿,你会以为那裤子是挂在一根晾绳上。再往上,是一件白色圆领汗衫,但说黄色会更加准确,它和军裤几乎浑然一色。两根像长丝瓜一样的手臂从袖筒里伸出来,右手握着一根丈把长的竹竿,竹竿正中扎着一根红布条。汗衫的圆领上是细细的颈根,这个地方倒颇像鸭脖子,只是没有毛绒绒的感觉,两根青筋从颈根上探下来,顺着凹陷的胛骨,闪电般探入领口内,消失不见了。让人心安的是,细颈根上的脑袋也不大,像一只倒立的紫茄子。五官俱小,小眼睛,小鼻子,小嘴巴,小耳朵,再加上小额头、小脸块、小下巴、小平头,这一切,把它鼻梁上的那副黑框眼镜衬托得很是威风,仿佛那里面藏着有关这个人的所有秘密,甚至藏着比这个人更多的其他秘密。 “叫肖叔叔。”父亲重复了一句。 “肖叔叔。”我轻轻叫道。 他笑着走上来,摸摸我的头,说:“长得好知识。”我则瞅见那鸭群里少了两只鸭子。他本来站在鸭群中央,我不知道他是如何跨过前面的鸭子来到我面前的。我与鸭子显然有一段距离。可我一眨眼,他就到了我面前,我猜想,他与鸭群之间一定有种惊人的默契。 “肖叔叔是高材生,你做作业遇到难题可以向他请教。” 父亲难得和气一次,这让我对肖叔叔抱有莫大的好感,何况他还带来一群好玩的鸭子。 肖叔叔连连摆手。他笑得很浅,浅得好像他不会笑似的。我这时松了一口气,我怕他马上要看我的作业,像刚才俯下身子的天那样,把我和万物笼罩在一片阴影中。还好,他没有天那么大的身子,我能够轻易摆脱他的阴影。 “我现在只会放鸭了。”肖叔叔说。他的声音低沉、沙哑,与鸭叫相似。 我笑嘻嘻地对他说:“你不是肖叔叔,你是鸭子叔叔。” 父亲立即将右手食指弯成栗凿,直向我头顶袭来。我身子一溜,像泥鳅样滑掉了。“没礼貌!”那个栗凿恶狠狠地在空中瞄准我。 “不要,不要。”肖叔叔捉住父亲的手,“他没说错,我现在跟一只鸭子有什么区别呢?” 三 父亲让肖叔叔把鸭子圈到我家后院。后院不大,数百只鸭子窝在里面,显得有些拥挤,但它们非常听话,走路时步调一致到只发出一种声音,叫时一起叫,吃时一起吃,大部分时候它们都很安静,比我们以前喂三四只鸭子还要安静。从屋前地坪、阶基到后院,人要穿过堂屋和厨房,鸭子走的却是猪栏房后面的一条阴沟,阴沟右边是父亲用土垒起来的一条绿化带,上面密密麻麻种着杉树,从这边望不到那边。只有几公分宽的一条阴沟,肖叔叔一声口哨,鸭子迅速整齐地排好队形,一只一只鱼贯穿过阴沟到了后院,前后不超过十分钟。 肖叔叔在我家住了好几天,隔壁和对门都不知道我家后院藏着几百只鸭子。我到匹超家里,骄傲地告诉他这一消息时,他一口咬定我是吹牛。我心里暗喜,因为,平时我和他打赌从未赢过。我问他赌什么。他自信满满地说,随便你。我说,如果我赢了,你得叫我班长,我叫你学习委员。他二话没说答应了。我把他带到家里,后院里一只鸭子也没有。匹超笑得岔不开气,脸急剧变形,红红的像一团烧得发软、遭到锤打的铁。我气愤地问妈妈,那些鸭子哪里去了?妈纳闷地看着我,答道,肖叔叔放到外面去了。我使劲对匹超说,听见没,现在是放鸭时间,放到外面去了!匹超鬼笑着说,那我不管,我没看到,就等于没有,班长还是我的。他扬长而去。我真想像抓一只鸭子那样把他抓回来。我这一想,数百只鸭子跑回来了。它们像河水一样,哗哗流淌到我的脚边。我赶紧再去喊匹超,他却已成为酸枣树上的一根树枝了。 那是村里最高的一棵酸枣树,连对面的罗岭山都没它高。没人敢爬到这棵枣树上去摘枣子,即便枣子熟得掉到地上,也没人敢捡了吃。村里人说,这棵酸枣树上结的不是枣子,而是天上的星星。其他树上只有夏秋季节长枣子,这棵树上一年四季都有;其他树上的枣子都生青熟黄,这棵树上的枣子一长出来就是发亮的。匹超胆子忒大,竟敢爬到这棵酸枣树上去,他真把那臭狗屎班长当天神了哦! 我对着高高的酸枣树上,那株叫匹超的树枝喊,你他妈的下来,我家后院的鸭子回来了!匹超直接掉到了地上,像一根被刀砍断的树枝,从树干上疾如流星地坠落。匹超把地面砸得陡然倾斜,我还没回过神来,就被掀翻在地,酸枣树连根拔起,直插云霄,枣子有如雨下,打得我全身酸痛。良久,天地无声,待我好不容易站起来,觉得自己变成了一棵酸枣树,长着僵硬的枝条、粗糙的绿叶以及酸得发痛的圆圆的枣子。 匹超成了一个瘸子。比罗岭山还高的那棵酸枣树死了。这都是肖叔叔来之后,我们村子里发生的大事。 四 匹超瘸了腿,他妈哭了,他爸唉声叹气,村里人除我之外无不替他惋惜。但三天之后,连匹超自己都适应了那条瘸腿。学校里曾传出是否让我接替匹超担任班长的议论。我的耳朵被这条传言弄得老大,像只猪耳朵耷拉下来。我不敢问我妈。但我妈的眼神告诉我,那是不可能的。匹超成绩比我好,他瘸条腿也是当班长的料。我死了这条心是一个星期后,公社开运动会,每班派三名同学去,我们班去的是体育委员、劳动委员,还有匹超;学习委员没份。我想,匹超瘸成那样他能参加运动会吗?没想到,他竟然拿到一个名次,神气得像捡到一根骨头的狗。原来,他腿短一截,跳高的时候正好没打着横竿,得到第七名。这个项目报得好,我平时练跳高,每次总是腿把横竿打下来,有些事情你不得不服。 肖叔叔看出了我的失落。他等我们全家都睡好后,就铺上席子睡在我家堂屋里。妈妈本来安排肖叔叔和我睡一床,肖叔叔死活不肯,他硬要睡在堂屋的地上,他说那里又宽敞又凉快。妈妈才赐给他一床芦苇席子。这一年秋天很热,跟夏天共穿一条裤子,共一个鼻孔出气。匹超从公社运动会载誉而归那天晚上,月亮照得我睡不着觉。天上的星、窗外的树以及田野里的蟋蟀全在开运动会似的,你争我夺,你追我赶,吵个没停。我躺在床上,发现星星们的运动会难度并不大,跑得慢,跳不高,蹦不远。我按捺不住,从猪栏房搬了一张梯子,搭在屋前的泡桐树上,嗖嗖嗖爬上去,我一口气报了所有项目,短跑、中长跑、长跑、跳高、跳远、立定跳远,等等。星星们不是胖子就是矮子,而且它们很不讲游戏规则,一顿乱跑乱跳。论不讲游戏规则,它们岂是人类的对手!我除开长跑没赢牛郎、跳远输给孙猴子外,其余所有项目都夺得了第一名。这跟匹超仅有一个第七名岂可同日而语!我一一领奖之后,志得意满地准备回来,却发现泡桐树下的梯子不见了。梯子不见了,我如何回家?虽然我刚刚勇夺跳远冠军,可从天上跳到地上还是太远了吧。 我隐隐看到自己的家,黑色屋脊像一只乌龟的背,淹没在时光的深水里。忽然,它慢慢地向前爬动。天啦,那不是我的家,而是一只真的乌龟。它朝时光的深水里爬去,马上要脱离我的视线了。我吓得大声哭叫,并一头栽下来,正好落进肖叔叔的黑边镜框里。如果不是肖叔叔的黑边镜框,我就会像上次匹超从酸枣树上掉下来一样,成为一个瘸子。 我的失落无可遁形。在现实中,天上的一百个第一名也抵不过地上的一个第七名,一个健全的学习委员敌不过一个瘸腿班长。肖叔叔黑边镜框里深陷的瞳仁将这一切尽收眼底。 五 第二天,学校放秋收假了。妈妈要我跟匹超他们一起下田割禾。我不喜欢割禾。大片大片的金黄被镰刀收割,无数金黄的脑袋和金黄的身躯惨遭毒手,仿佛突然消失在天际的鸟群。每次我割禾的时候,锋利的镰刀伸出去,左手抓住一把稻子,就像扭住一只鸟或者一只鸡鸭的脖子。我感受到稻子的鲜血喷涌而出,溅得我满手满身都是。每天回去,我泡在屋前池塘里,恨不得用一袋洗衣粉来搓洗全身。我在秋天广阔无边的丰收景象里闻到血的气味、死亡的气息。 我提出和肖叔叔一起去放鸭子,妈妈把决定权交给父亲。父亲的脑袋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严肃,一面滑稽。严肃的那面是脸,他的脸上很少有笑容,宛如一块牛毛毡;滑稽的那面是后脑勺,他的后脑勺有一个耸起的岬角,乍看好像永远戴着一顶尖尖的黑帽子。父亲点了点他严肃的那面,同时也扬了扬他滑稽的那面。 我和肖叔叔把鸭子赶到河边。我从肖叔叔手里抢过那根丈把长的竹竿,走在鸭子队伍中间。鸭子们似乎不喜欢我,它们前所未有地鼓噪起来。我的身体太小,控制那么长一根竹竿的确有问题,这不,竿尖不小心敲到了一只鸭子的头。鸭群中迅速发起骚乱,有的向我扇动翅膀,有的用脚狠狠踩我,还有一块石子向我扔来,还有一只装作匹超瘸腿的样子来吓我……正当我手足无措,肖叔叔一枚尖厉的口哨让全场鸦雀无声。接着,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他声色俱厉地对鸭子讲了一通话,我一句都没听懂,只看到鸭子们一个个服服帖帖,它们缩着脖子,眼里露出惭愧、慌乱,甚至是惊惧的神色。 鸭子们排着队下河游泳去了。我问肖叔叔,你刚才跟它们说了些什么。肖叔叔羞涩地笑了,仿佛做了一件不值得张扬的事。原来,他说的是鸭语。他告诉鸭子们,你们是来做客的,一定要遵守革命纪律。我惊问,鸭子也有革命纪律?肖叔叔笑得更羞涩了,但羞涩中掺杂了难以言喻的坚定,好像把一袋水泥倒入水中,经过笑容的搅拌,愈加凝固。我只好用问话再注些水进去: “你给它们定了哪些纪律呢?” “纪律多着呢。第一,热爱集体,助人为乐,有主人翁精神;第二,秋毫无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有,不得调戏当地母鸭。违反的统统划为右派,召开批斗会。” “哈哈,鸭子也开批斗会!鸭子是怎么开批斗会的?我很想看看。” 这句话不期然触到肖叔叔的痛处。他一直控制在脸上的笑哗一下流进河里,成群的鱼跑过来,聚集在我们脚下,以为找到了上好的食物,但围着我们脚下打转转,嘴巴朝天撮起,仍然只能饮到寡淡的河水,倏忽又无影无踪,少数没来得及脱身的,被队伍后头的几只鸭子吞进腹中。队伍前头的鸭子发现了后头的动静,立马掉转鸭头,蜂涌过来,河面上溅起很高的浪花,仿佛投进去一颗炸弹。 我抬头看着肖叔叔。他的眉头拧成两座山头,相距不远,却互相不卖账;眼球像要冲出黑边镜框,成为两只滚动的车轮;鼻尖上不知怎地挂着一粒水珠,这增添了他整个五官的亮度,使它具有一种神秘感和神圣感。我们用小圆镜反射太阳光,照在屋内墙壁正中毛主席像的鼻尖上,就是这种效果。每当这个时候,我们不是顽皮,而是更加崇拜伟大领袖,因为没有任何人的鼻尖能够经受我们如此长时间的照射。自身没有足够光芒的人,是受不了这种强光的。打个很简单的比方,如果我用同样方法去照父亲的鼻尖,一定会遭到一阵痛打。我们热爱毛主席。这不是没有道理。他老人家挂在墙上,天天让我们照,却总是布满一脸仁慈的笑。 除了毛主席,我现在第二崇拜的无疑是肖叔叔了。他鼻尖上的水珠开始放光,光线越来越强,照在河中,变成满河金光。那些飞溅的浪花一遇到金光,立马散落开来,不复有升腾的力量。鸭子的喧闹戛然而止,好像这条河里从来没有过一只鸭子。肖叔叔鼻尖上的水珠终于掉下去了,强烈的金光恢复成平常的日色,河里的鸭子又排成了整齐的队列。 肖叔叔的眉头舒展成一片辽阔的草原。在他窄窄的脸庞上,那片草原经过太阳穴,向下延伸到鬓角,向上蔓延至发梢,向前钻入黑边镜框内,向后连接后脑勺的大部分地区。在这片辽阔的草原上,肖叔叔的小嘴,像一只袖珍喇叭,发出嘹亮之音: “你们这样子乱来能改造好思想吗?你们心中时刻泛起那些肮脏的念头,时刻以为纪律是对你们的压制,时刻以为自由就是忘乎所以,就是每天在吃饱睡饱的同时,纵容自己的贪欲。你们成天泡在水里,却不曾洗过一个干净的澡,我三个月不洗澡都比你们干净。畜生啊,我把你们当人看待,世界上只有我把你们当人看,给你们制订标准,划分左派和右派,让你们执行正确的路线。难道你们……” 说到这里,肖叔叔蓦然停下来,他望着对面的罗岭山,有一条弯弯曲曲、细如鹅肠的小道挤在半山间,它从山脚一直爬上来,累得直不起腰,一头扎进密密的丛林里,仿佛被人随手撂在那里的一截鸡肠。从我的视角看过去,肖叔叔扬起的手正好抓住了那截鸡肠,似乎要将它当作演讲的最后一个铿锵有力的句子。但这一句我始终没听清。 演讲结束了。我和肖叔叔再没说话,我的全部身心、我身体的每个毛孔,都灌注着对肖叔叔的无限崇拜。那时,我愿意做他竹竿下的一只鸭子,哪怕是一只病鸭、跛鸭、老鸭、幼鸭。我对那截鸡肠充满渴望,也许正因为我没有听清,我总是寻思着它的奥义。一如它在山上,能延伸至某些隐秘的角落,甚至能翻越大山,它在肖叔叔铿锵有力的演讲里,同样能揭示某些我无法理解的东西。 六 又发现了异样!不是父亲眼光的异样,而是家里的气氛生出了异样。像一锅烧得喷香的饭,多了一灶火,便散发糊味来。妈妈对肖叔叔住着不走生了意见,她时常跟父亲在私底下嘀咕。我非常关注事态发展,他们不可能瞒住无所不在的我。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磋商的结果,内心又希望他们不停地磋商下去,永远也没有结果。 我听出了一些苗头。肖叔叔竟是右派!去新疆坐过十五年牢,前年才刑满释放。他回到家里,娘疯了,弟弟死了,妹妹嫁人了,就当起了“鸭司令”。我没听爸妈谈起肖叔叔的父亲,难道他没有父亲?也许是我听的过程中漏掉了。 妈妈怕肖叔叔的右派身份对家里不利,住一两晚反正是做客,住久了别人还以为你们同情右派。父亲说,人家刑满释放就应该摘帽了,况且我们不说,谁知道他当过右派!他没个家,也不容易,让他住些日子吧,读大学时我们玩得最好,我经常去他家吃他妈妈做的糍粑,味道比肉还好。妈叹了口气,没做声。 不料,三天后,事情发生了重大转机。大队革委会号召批斗地主汪三婆,全村热闹得像个大戏场。很早,妇女们就聚集在大队部,用两块巨大的黄草纸拼起来,裁剪成一件旗袍。 这样的黄草纸我们一般买来切成方条,搁在茅厕的一个破盒里,揩屁股用。我喜欢闻它里面那种草的气息,每次蹲在茅厕板上,我就不想下来,陶醉于黄草纸那种干草与纸浆混合时所汇集的金黄的歌声。我将一张张黄草纸凑到鼻前嗅,放到耳边听,用眼睛细细地看,然后,我双手捧住它们,蒙住我的脸。我闭上眼睛也能看到那种黄,它粗糙的表面后藏着一个个威武的猛士。每当拿起其中一张去揩屁股时,我就想象会有这样一个猛士从屁股眼里钻进我的体内。有时,我扭头去看,真的看到一个身影一闪,消失在粪缸边沿与苍蝇翅膀的缝隙间,融入外面徐缓而浩荡的秋风中。 上午十点,地主分子汪三婆被四五个精干的民兵押上了学校礼堂的舞台。她已经穿上了妇女们为她缝制 的那件旗袍。头上顶着一个同样是黄草纸做的又长又尖的圆筒帽,戴上这顶帽子,让她几乎长高了一倍,成为整个舞台上最高的人。但无论如何不会让她最高的,这不,一块大木牌挂到了她的颈根上,她不得不低下头来。木牌上的字不看我们也背得出,那个红色夺目的“×”无数次被我们移植到同学甚至老师身上,倾泻着我们的怨恨之气。 汪三婆一个人住在村尾一间破落不堪的瓦屋里,从我看到她的时候起,她就是一个人,一个头发花白却仪容整洁的老妇人。我以为她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生下来就是一个人,一个头发花白却仪容整洁的老妇人;生下来就是地主,就要戴高帽子、挂木牌子挨批斗的。我觉得她运气太不好了,生成这个样子,好像生来就是一只老鼠或者一只苍蝇,人人喊打,藏着躲着都要被人打掉。 大队革委会主任主持批斗会。我妈站在舞台右侧的前方,负责领喊口号。民兵营长带领一伙民兵手拿扫帚、木棍、扁担,分站在“地主分子汪三婆”两侧。匹超的父亲第一个跳上台,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口水地愤怒控诉汪三婆的滔天罪行。接着,杨二狗的爷爷、刘小凤的奶奶、周长庚的大伯、陈立生的姑妈、张跃进的婶婶……纷纷把自己的鼻涕、眼泪和口水贡献出来,向汪三婆发起猛烈的革命进攻。 每个人讲完,我妈领喊口号:“坚决打倒恶霸地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血债要用血来还!”她每喊一句,台下人跟着喊,只有站在汪三婆两边的民兵例外,他们要用手里的扫帚、木棍、扁担侍候她,让她跪在地上,享受击打带来的暴风雨般的疼痛。 平时,我也会和匹超他们一起,自豪地跟着我妈喊口号,一边叠着纸飞机往天下扔。这天我没有,我被汪三婆身上的黄草纸旗袍吸引住了。这是那帮妇女们做得最好的一次。她们在这件集体创造的作品中,融汇进了源于日常生活的熟练、聪慧与好奇,多么心灵手巧的作品啊。旗袍的确是为汪三婆量身定做的,窄肩,宽袖,袍长,衬短,腰部微微收束。在聚集了数百人的吆喝与扩音器扩大数十倍的仇恨里,旗袍粗糙的表面被磨砺得闪闪发光。 仿佛听到一声号令,礼堂外面顷刻暗淡下来。天俯着身子,好像要挤进这喧腾的礼堂里。在巨大的阴影笼罩下,我看见那旗袍浓缩成炫目的亮团。汪三婆跪在地上,棍棒、扫帚划出的精妙弧线将她团团围住。她的五官渐渐退出面庞,先是耳朵变成一缕微弱的声音飞走,然后是鼻子化成了浓浓的气味,接着是眼睛连同眉毛被阴影压迫着,跌落进旗袍的领口里,最后是嘴巴,在失去血色之后,隐入从喉管迸发出的最痛的一个语词。当这一切消失,舞台上只剩下了那件旗袍,一件跪着的黄草纸旗袍,以它独具一格的生命特征,支撑起一种无比伦比的壮美。 我热血沸腾,又感到不可言喻的恐惧,像一只即将受伤的小鸟,惶然面对射向自己的弹弓。这时,外面突然响起整齐划一的“踢踏踢踏”声,像是大水从罗岭桥下的河里蹿入田野,褐色的水脊一浪高过一浪。很多人站起来,向外面使劲张望,我太熟悉这种声音了。我刚张开嘴巴,想发布独家消息。肖叔叔的鸭群就鱼贯而入,大摇大摆地在礼堂后面排成棋盘式的方阵。 七 革委会主任呆若木鸡,在扩音器前顿时失声。我妈捏着一张口号纸,也不知所措,她保持着一种奇怪的口型,似乎在教台下数百人跟着她“啊,啊,啊”。民兵营长的木棍举在半空,直插入阴影深处,仿佛天的巨手死死揪住了那头,令他不能动弹。 全场阒寂。 我情不自禁地喊道:“肖叔叔!”其实,我压根儿没看到他。我和匹超他们挤在前面,加上鸭群进来时,大人纷纷站起来,所以,我们这些小孩被陷在大人身体所组成的深井里。但我知道是肖叔叔来了,他放鸭放到批斗会现场来了。我看到肖叔叔时已是一分钟之后,他幽灵般地闪到了台上。村里很多人见过他,也知道他是我家的客人,对他和鸭群的闯入除了有些唐突之感,并无恶意,反而因为这一戏剧性变化,使得批斗会增添了更多娱乐元素,他们倍感欢欣鼓舞。 革委会主任一时讲不出话来,只好将喉咙对着扩音器干咳,以显示他的存在,效果却不佳。他的脸色开始与天色达成一致,用大面积灰霾布控,可舞台最前面那金黄色的亮团如一条火舌,吞灭了他的阴沉。我妈看在眼里,她面露不悦地问:“老肖,你到这里来干嘛?” 肖叔叔没回应。他手里长长的竹竿一挥,嘴里吹出一声遏云裂帛的口哨,立马雄赳赳、气昂昂地上来一队鸭子。它们一齐伸长蛇一样的脖子,扑腾着两面形似旗帜的翅膀,瘦而有力的脚蹼快速划动,使整个身体像一条轻浮的小船。它们的眼珠鼓凸出来,脸上似笑非笑,扁扁的长喙有如一个额外加置的淡黄色道具,与鸭子本身无关。 这队鸭子在肖叔叔持续而不断变换的口哨指挥下,站到了汪三婆身后。民兵营长不由得退后几步,瞪大眼睛,狠狠看着这些取他而代之的畜生,恨不得踹上几脚。 民兵营长出脚尚在意念之中,肖叔叔赶紧将自己的嘴撮成喇叭形,脖子伸长,眼珠鼓凸,脸上似笑非笑,两只手像蹼在水里一样上下划动。划着划着,猛地双手一拍。随着这一声响,鸭子们如离弦之箭,迅即冲向那跪着的黄草纸旗袍。它们有的爬上身,从宽宽的领口溜进去;有的从袖管向里面突进;有的矮着身子,匍匐在地,在裤脚处找到一条秘道……这些在草丛、田野、河边、山地里扫荡惯了,拥有强大团队精神与个人战斗力的鸭子,很快占领了它们的阵地。它们在一个年迈的女人身上,照样找到了自己习惯生活的草丛、田野与河边山地,并为所欲为地发出放荡的叫声。
【编者按】这是发生在过去那个特殊时代的故事。故事中的“我”刚刚上四年级,对于外面的一切都是那样懵懂。当肖叔叔出现在“我”生活中的时候,“我”只是好奇他瘦骨嶙峋的身体,而不知晓他的来龙去脉。之后慢慢“钦佩”他独特的才华,那“鸭语”调动了整个鸭群。让这些不是人的鸭子,拥有跟人一般的行为。仿佛表演一般。各自有各自的位置。在对待汪三婆的时候如此,对待头鸭时如此,对待他自己也是如此。这些对于“我”来说,都是如鸭语一般,听不懂,也看不懂。 小说字字裹挟着时代的色彩,浸润着时代的悲凉,回荡着无声的控诉,溢满对过往的恐惧。如那倾压过来的乌云,时常笼罩着,让生活暗无天日。小说紧抓人物和鸭子的特点,描写生动,情景交融,紧扣中心,结合生活,令人好似置身其境,引人无限沉思。问好作者,佳作,推荐共赏!【编辑:平淡是真】【江山编辑部精品推荐013052624】 |
|
|
|
||
逝水流年
|
2014-04-16 10:12:17
恭喜吴昕孺先生,感谢您对逝水流年文学社团的支持!
|
|
|
|
||
芦汀宿雁
|
2014-04-16 10:14:10
热烈祝贺吴老师佳作获得荣誉。
|
|
|
|
||
平淡是真
|
2014-04-16 10:19:43
好荣幸,这篇文章是我编辑的。再看,依然感觉非常好! 祝福吴老师,感谢老师一直支持流年。 |
|
|
|
||
纷飞的雪
|
2014-04-16 10:21:30
恭喜昕孺哥哥佳作获奖。 一直以来,有你的支持,是我办好流年的动力! 感谢兄长,祝福兄长。
|
|
|
|
||
孤独舞者
|
2014-04-16 10:39:38
祝贺吴先生佳作获奖!
|
|
|
|
||
了缘无尘
|
2014-04-17 11:15:47
热烈祝贺!!!
|
|
|
|
||
你猜
|
2014-04-17 19:18:23
祝贺吴先生佳作获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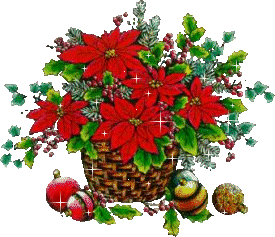 |
|
|
|
||
辽宁娴雅
|
2014-04-17 22:12:52
热烈祝贺吴先生作品获奖!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