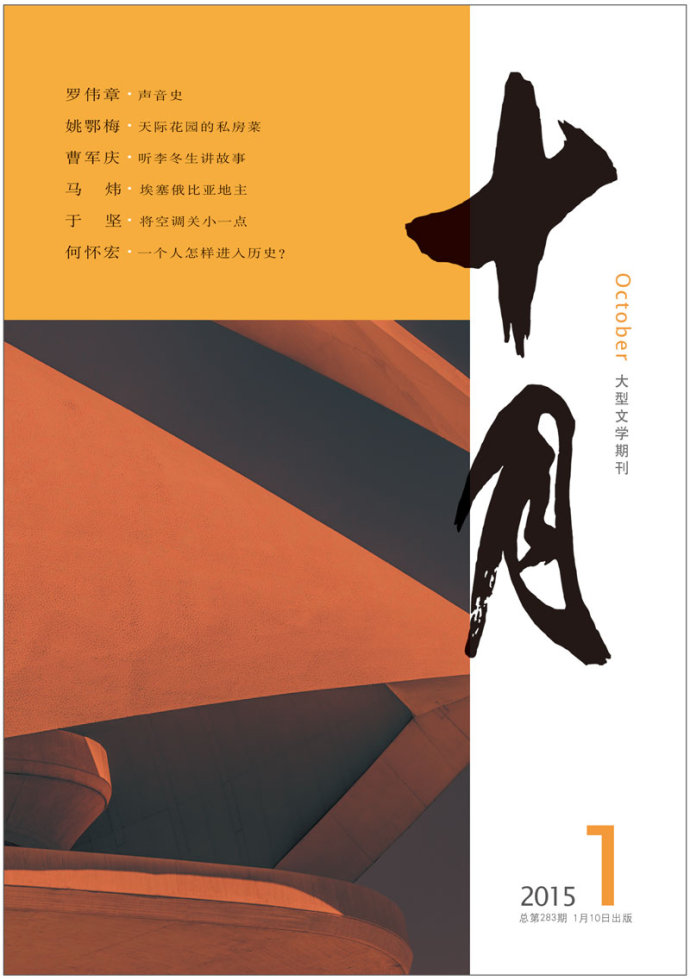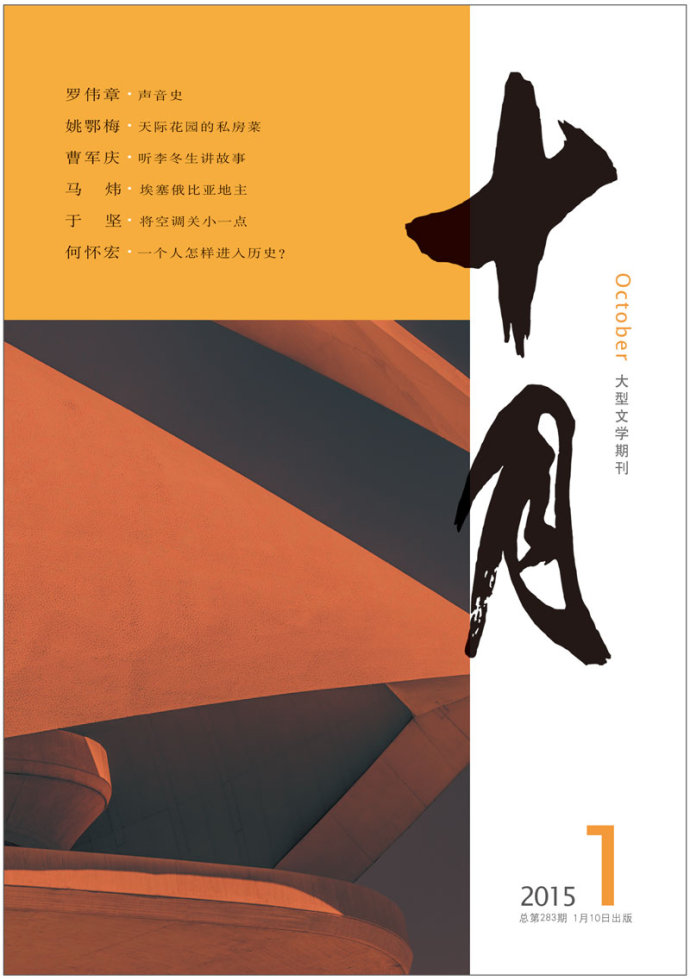
本社讯
逝水流年文学社团专栏作家王必昆先生
散文《行走的翅膀》刊发于《十月》2015年第1期。

【流年】行走的翅膀(散文)
作者:王必昆
http://www.vsread.com/article-371831.html
一
天粉粉亮,鸡鸣戒旦,村庄醒了。
其实村庄也并没全醒,最早醒来的只是孩子,上学的孩子。
孩子们走出村庄,走在山路上。山路被孩子早早踩醒,一脚一脚的,尘土脱屑,露水积浸,有些疼。
山路是山民走出来的。狗认主,路也认主。瘦弱的山路会把孩子从这个山村带到另外一个山村,一个有学校的山村。清晨带出去,傍晚领回家。
乡村的孩子每天就这样去求学。路有多远,心有多远;路有多疼,心有多疼。谁也无法计算,一个孩子读完小学,要把那条山路走多少遍,合起来有多远,拉伸了又有多长。而这样的行走,孩子们却仍然难以走出乡村,始终在起点徘徊。只是加深了疼痛,磨糙了童年。
二
我上小学时,咱村的小学是完小,从一年级办到五年级,不用出凤尾村就可读完小学。到我小妹上学时,学生越来越多了,咱村的小学却只办到三年级,从四年级起即要到大队上的石洞小学读,还要增读六年级。从我们凤尾村到石洞村,有两公里山路,路边山坡上都是坟地,阴气很重,平素少有人走。我小妹她们那一拨学生,每天上学就相互耍闹恐吓着一路奔跑,生怕落在后面。那时也不带饭,中午仍跑回家吃。说是走路,其实是小跑,每天来回四趟,约八公里山路,春夏秋冬,走读三年。
那时的村寨,无论大小,都有一所小学,哪怕是在破庙里,至少也要办到三年级。像我小妹她们那样,从四年级开始,才到原先叫大队后来叫办事处再叫村公所现在叫村委会的村子上学。
而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普遍的村庄没有学校,普遍的农村孩子从一开始上学就要走读,再远的就寄宿。村里的一所所小学被撤并闲置,过去是教书育人的地方,现在沦为六畜兴旺的场所。没有学校的村庄变得更静,静得死寂,再也听不到朗朗的读书声。那些瘦得如蛛网一样连接村与村的山路被拾辍起来,每天被孩子拉扯,或拉扯着孩子,来来往往,踏来踩去,直到把陌生而粗野的山路走熟走疼。这些山路,原本是村民出山干活或 走村串寨找亲戚才走的,现在竟变成了孩子的求学之路,一条条如诗一样痛苦的求学之路。
我寻访到小河边,一条因连年干旱而干涸的小河边。小河两岸有村落,村名就叫小河边。这是建水县岔科镇初达村委会的所在地。初达村委会辖十二个自然村,过去各村都有学校,2007年校点撤并后,整个村委会只保留小河边小学一所完小,十二个彝族村寨的孩子全集中到一个村来上学。从学前班办到五年级,六年级还要到更远的镇上就读。
老教师亚田富心酸地告诉我,小河边小学二百七十个学生,走读、寄宿基本各占一半。距校三公里内的走读,三公里以上的寄宿。除本村小河边外,学生需走读上学的有坝头、初达、下幸、冲尾四个村的孩子,寄宿的有克地、莫舍租、勒渣、铁牛山、梨花尖、禹堵、设水七个村的孩子。学生走的全是山路、土路。我去时,正值下雨,看见不少孩子把布鞋脱掉赤脚走,泥滑路烂的,孩子们怕把仅有的一双鞋走脏走烂了,舍不得穿鞋。
要说边远,菲租克算得一个。如果不是曾经在那里生活过的朋友杨华带路,我大约一辈子也来不到这样的山寨。说的是屏边县新华乡菲租克村委会,这个村距乡政府十九公里,距县城一百一十二公里,很多彝族、苗族村民,一辈子没去过屏边县城。那是一个苗族自治县,全县没有一平方公里平地,全是大山。我刚工作时在过几年。现在我看到的菲租克小学前两年刚翻修过,砖木结构,红平瓦,四排平房围成一个院子,院子的空地就是篮球场。但学校修好后即遇撤并,只办一、二年级,共有四十八个学生,用了两间教室,其余全空着。于是村委会、村党支部、村卫生室、农家书屋等机构全搬进学校里办公。大门口挂满了牌子,而学校本身却没有牌子。菲租克村委会辖六个自然村,这六个村的孩子上学要到整个村委会唯一的菲租克小学走读,但只能读两年,三年级起还要走到更远的另外一个村委会的阿母黑小学就读。菲租克村委会有二百六十多户人家,每家的学龄儿童都要走很远的山路到菲租上寨的小学读书,而到阿母黑读完小时,最近的也要走七、八公里。
在边疆山区,学校的教学时间也不统一,得根据当地的乡村经验来决定。我看到菲租克小学星期六、星期日都上课,而星期一、星期二休息。说是逢星期一学生要和家长去附近较大的阿母黑赶集,老师也要去赶集,距县城和乡上都太远,村民能走路去赶集做买卖凑热闹的地方只有阿母黑。菲租克小学中午没有午休时间,师生吃完午饭就接着上课,到下午两点半就放学了。说是孩子小,离家远,路难走,给孩子早早放学回家,老师和家长都放心。
那天下午三点左右我们从菲租克回蒙自,一路上全是放学回家的小学生。开车三个小时走了几十公里山路,每段路上每个时段都有步行的学生,大约就是各个学校放学的时间不同而形成。一路上观察走路的孩子,就可知他们来自哪个村寨,在哪所小学上学。看到从阿母黑村里出来,回菲租克方向的,都是爬坡,走得很慢。看到从黑拉冲小学出发,往东边沿公路走的,就知道是几公里外的石马脚、亦打菲村的孩子。沿途一直到庄寨,到芷村,到小东山,到东村,进入蒙自城,都有随西下的夕阳徒步的孩子。红领巾,书包,饭盒,雨伞,这些走读学生的随身物件,一样也不能少。原来星星一样洒在大地上的村庄是由山路串结起来的,蛛网一样牵连的山路是由孩子走活的。没有孩子,没有走路上学的孩子,这些山路就更寂寞了。只是我情愿这些山路寂寞如初,哪怕一直寂寞下去,而不要让瘦小的孩子来踩疼瘦弱的山路。
三
跟随校长周劲松,我去了他的白巫山小学。所在地为个旧市保和乡白巫山村委会,辖五个自然村,我们落脚的小咪勒距乡上有三十公里,可见其偏僻。从锡都个旧出发,羊肠九曲,沿途经过了很多村寨,杨家田,乌谷哨,风筝山,八里寨,头道水,卡房,火把冲,梨花寨,大寨子,大咪勒,小咪勒。每个山寨都孤傲地矗立着几棵巨大的古树,藏匿着如古树一样寂静的山野风光。蓝天,白云,苍翠的森林,逶迤的群山,涂抹着与都市决裂的美景,馈赠给贫穷的山民,一份来自大地的礼物。
白巫山小学有两个校点,一个是小咪勒,一个是白巫山。校长住在小咪勒。我们到小咪勒小学住下。这个小学生源不多,实行隔年招生。小咪勒校点只招小咪勒村的,不用走读。现在上学的是二、四、六年级,共有三十五个学生。白巫山校点招收白巫山、柏枝木、姆初德三个村的学生,在读的是一、三、五年级,共有四十六个学生。这个村委会除小咪勒、白巫山的孩子在本村上学外,另外两个山村的孩子都要走几公里山路到白巫山小学就读。最远的是姆初德村的,要走五公里。白巫山对面的大山属于元阳县,山脚即是红河。这一带群山耸立,交通极为不便。挂在山上的村庄都看得见,但大半天也难走到。正如山民所说,对门听鸡叫,走拢要一天。在大咪勒,周劲松就指给我们看见了远处的小咪勒,藏在绿色的群山中,遮在白色的云海里,还有一片郁郁葱葱的楠木林,恍若仙境。但大自然的美景只能远观,若要近看,就不完美了。倘若在山村生存,那一呼一吸,一步一行,则都是挣扎。
周劲松对我说,白巫山小学走读最艰难的是姆初德的学生。姆初德是个纯粹的彝族山寨,只有二十多户人家。以前有学校,他就在姆初德小学教过书,后来撤并了。白巫山在山坞里,姆初德在对面的山崖上,相互能看得见。但隔山喊得应,走路要半天。从姆初德到白巫山原来没有路,因为上学,村里瘦弱的几个孩子走草稞,钻石缝,过山沟,几年下来才走出一条不像路的山路。这条山路连大人都不走,只有学生走。遇放假,学生休息,路也就歇息了。周老师都不清楚准确的距离有多远,只知道孩子们要走一个多小时。我查了一下,两地相距五公里,但实际的山路,应该比这更远。
周劲松老师反复说,从姆初德到白巫山那条小路,真的很危险,老师最担心学生在路上出事。学生早上八点前就要到校,下午四点半放学。其实这个小地方与制定政策的大地方实际有着一两个小时的时差,小地方的太阳起得晚,天亮得迟。姆初德的学生每天凌晨六点多就要出门上路,在冬季天都还没亮,有时候还得带电筒。山里湿度大,露水多,草稞深。孩子们早上从姆初德走到学校,鞋子、裤子甚至上衣全被露水打湿,遇下雨更是又湿又泥。每天早上白巫山小学的老师都要忙着烧一堆柴火,给姆初德的学生烤火,直到把衣服烘干才上课。遇到下大雨,山间电闪雷鸣,几个孩子爬行在山路上,老师和家长的心也一直纠结在山路上。他们担心山洪暴发,担心孩子滑倒摔伤。所幸几年来,姆初德的孩子在上学的路上都未出过事,这些孩子太坚强,太勇敢。
在教室里,老师带我看到了来自姆初德的五名走读学生。一年级:黄建成,男,六岁;吴春雨,女,六岁;白舍保,男,七岁;三年级:黄健,男,九岁;杨马丽,女,十岁。这是五个真实的孩子,真实地在姆初德山路上走读的小学生,他们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这样的事例越真实,越是残酷得让我心痛如绞。这几个矮小的小学生,个子只有城里幼儿园小班的孩子高,却要独自跋涉如此艰辛的求学之路。流泪的人,常常都是不能改变命运的人。而能改变山村孩子命运的,却是些不会流泪的人。面对这些弱小的孩子,你不知道如何帮助他们,又能帮助他们什么,只有暗自神伤流泪。我多想一个一个抱抱他们,但看着孩子胆怯的表情,又怕这些原本缺乏温暖和关爱的孩子,不适应陌生人的感情表达而受惊吓。
马文卫老师曾经在一个山区小学教过书。有他引路,我们到了开远市小龙潭办事处则旧村委会的则旧小学。小龙潭是个坝子,一个大型露天煤矿,而则旧村则在山顶上。则旧小学办到四年级,学生读五年级要到山下的小龙潭中心校上学,距离十五公里,需寄宿,走路要三个半小时。现在则旧小学有八十多个学生,三个老师。除则旧村的学生外,来自石洞、小矣那味、红坡头、树猴几个村的学生需走读,都是几公里的路程,最远的树猴要走三个小时。
在开远的另一片山区,我还去了大庄乡桃树村委会瓦白白村小学。瓦白白小学从学前班办到三年级,现有七十三个学生,四个老师。从四年级开始,瓦白白村的苗族、彝族孩子就要到桃树完小走读,有五公里山路。桃树村委会有十七个村民小组,包括瓦白白在内的各村的孩子,在读到高年级时都要到桃树完小走读。桃树完小校舍不够,只能寄宿六十多人,在那里读书的孩子多数都是走读生。
即使再枯燥,我也要列出这些查找到的数据,因为这些阿拉伯数字满含血泪,戳得我心疼,承载着几亿农民的痛苦。根据教育部公布的统计数据,从1997年到2010年的14年间,全国减少小学371470所,其中农村小学减少302099所,占全国小学总减少量的81.3%。2000年,全国农村小学数为440284所,而到2010年则只有210894所,10年农村小学数量减少了52.1%。那些被疯狂撤并掉的小学,我敢说,大量都出自广袤的西部农村。
过去有炊烟的地方就有学校,现在我走遍多少大地上的村庄也见不到几所学校。这样的校点撤并,纵然你说出一千个有利的理由,但面对我所进入的现实,我和乡亲们只有无尽的悲伤。
……
【编者按】一字一句地读完这篇散文,心中只余一个“疼”字。“行走的翅膀”,翅膀不能用来飞翔,只能用来行走,这是怎样一种怪现象?跟随着作者的脚步走进山区,走入乡村,我明白了:生活,有着太多的无奈;山村的孩子,有着太多的苦痛。
由于交通不便,小小年纪的他们,为了上学,只能用瘦小的脚板奔走在瘦弱的山路上。校区合并政策实行以后,这些可怜的孩子们只能住校,接受所谓的“封闭式”管理。诚然,自理能力提高了,可他们幼小的心灵受到的创伤何人来弥补?他们走得累了,只能以那些没有安全保障的马车、摩托、拖拉机、微型车、农用车来代步,甚至有的要骑马和溜索上学。这,给他们的安全埋下了极大的隐患,近年来,屡有媒体报道的校车事故,其实,学校本就没有车,何来校车?学生乘这些车上学,人身安全怎能得到保障?可一旦出车祸,谁也不会反思造成事故的真正原因,责任只能由农民驾驶员来承担,教育局的官员也只会在接受采访时则重申:禁止学生乘坐马车、农用车、拖拉机上下学。没有人真正为孩子的处境设身处地地着想。“乡村的孩子啊,那是与大地最亲近的精灵,与疼痛最密切的诗歌”,看到这一句,我的心颤栗了,同样是活泼可爱的孩子啊,城乡的差距,却在他们一出生时就将他们身上打上了贫穷的烙印,城里的孩子在大手大脚不把金钱当回事的时候,山村的孩子却只能以填饱肚子为目标。尽管国家有补助,孩子们有了营养餐,可这可怜的补助钱又有多少真正到了孩子们嘴里?云南、广西、贵州就相继曝出食物中毒问题让人寒心。
不但是孩子,山区的每一个年轻老师的处境,也同样让人心疼,他们都是没有背景没关系的农家考上大学的孩子,进入城市对他们来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且不说农村考生的分数线永远比城市孩子的高,且不说各名校招生时都以本城市考生为主体,即便他们挤上了那座独木桥,没有关系没有背景的他们想留在城市也只能是无望的奢求。最终,他们只能考入城里孩子看不上的山区学校,在这里奉献着自己的青春,留下一个个感人的故事。如那个叫纳玉莲的老师,她是一个伊斯兰教徒,在教义中,猪肉为不洁之物,可是,山村每家每户都养猪的事实让她无法和村人交流。
纯朴的村人为了留下这个好老师,竟集体拆了猪栏,改为养羊。这个故事引出了我的眼泪,这个举动也牵住了纳离开的脚步。贫穷的山村,不知有多少像纳这样的老师,不知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他们在给山区的孩子带来希望的同时,深深埋藏着自己的苦,以幸福的姿态绽放着青春。这是一篇贴近生活的极富感染力的散文,文章语言朴实生动,情感真挚自然,大量走访得来的活生生的事实展现了山里孩子求学的不易和山村老师的无奈,字里行间流露出渴望给孩子们一份公平公正的生活的愿望。值得每个人深思细品的好文,欣赏荐阅。【编辑:素心如玉】 【江山编辑部·精品推荐1310260009】
[作者简介]

流年专栏:『紫色雨露』
江山文集:http://www.vsread.com/space/myspace-30889.html
注册日期:2013-01-28
简介:王必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十三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在《十月》《中国作家》《文艺报》等发表过作品若干,有文章被《读者》《散文选刊》等转载。著有散文集《大农门》、诗集《紫色的雨路》、报告文学《云岭红墙》等。曾获云南文学奖、滇东文学奖、在场主义散文奖等。现居云南红河。
《十月》2015年第1期
目录
中篇小说
声音史 / 4/4 罗伟章
天际花园的私房菜 / 96/4 姚鄂梅
坦桑石 / 172/4 光 盘
短篇小说
听李冬生讲故事 / 65/4 曹军庆
埃塞俄比亚地主 / 121/4 马 炜
归乡记 / 128 方 如
宜居之地 / 136/4 常聪慧
小说新干线
小河夭夭(中篇) / 143/4 小 昌
浪淘沙里有个万青青(短篇) / 143/4 小 昌
乡间的小径也分岔(创作谈) / 168/4 小 昌
印象·小昌印象 / 170/4 李约热
散 文
将空调关小一点 / 73 于 坚
逝水沉思 / 192 行 者
行走的翅膀 / 201 王必昆
思想者说
一个人怎样进入历史? / 85 何怀宏
中国科协 中国作协主办
科技工作者纪事
花儿与少年 / 214 玄 武
诗 歌
余笑忠的诗 / 228 余笑忠
忏悔录 / 231 王明韵
沉默无可替代 / 233 黄沙子
植物颂 / 235 葛筱强
时光之羽 / 237 亚 楠
诗四首 / 239 陈智勇
艺 术
彩色插页 阮国新的山水画
封 三 静物(油画)徐 里
封面设计 赵平宇
篇名题字 谢有顺